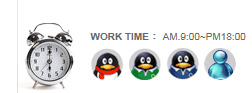1642年,波士顿(北美清教徒殖民统治下的新英格兰)监狱前,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子,抱着三个月大的婴儿(朱厄尔),站在行刑台上,等待着对于神权政治的查尔斯来说。文教(常译为清教徒)政权在公众面前宣布了对她“通奸”(红字“A”的英文首字母:Adultery)的判决。
那么这个“罪人”是谁呢?
为什么要公开审判?
“通奸”有那么大罪吗?
如果时光倒流几年前,你就会知道,这个名叫海丝特·白兰的女人出生在没落的英国贵族家庭,却嫁给了一位“畸形”的老学者。当她决定搬到波士顿时,在途中,她的丈夫“失手”,据说被“野蛮”印第安人绑架了。他生死未卜,她只身来到波士顿定居。
正是在这一时期,她与当地德高望重的年轻牧师阿瑟·丁梅斯代尔相恋,并生下了“爱情之子”——珀尔。然而,就这样,在这个“清教徒”控制的“家”里,她犯下了教义中的“一诫”,即通奸罪,于是她被关进了监狱,然后被公开审判,被羞辱了。三个小时,并且“必须”终生佩戴。红色“A”作为惩罚。
故事至此,或许充其量只是对一段不恰当、应得的、令人满意的“婚外情”的描述,但后来的发展却大大偏离了一般的传统轨道。
随后,女子白兰的丈夫出现了。为了维护自己的“尊严”(毕竟广泛宣传太丢脸了。),他改名奇林沃斯,假扮医生,接近自己的“情人”亚瑟,不断使用各种手段使他的身体和精神都变得虚弱。他们都受过折磨,所以乐于“报仇”。
但结果却显得很“违规”。是的,最后,亚瑟牧师最终走上了刑台,将“真相”公之于众,完成了自己的“救赎”,然后死去,而齐林则“失去”了复仇的目标。一年后沃斯抑郁去世,甚至留下遗嘱,将自己的财产“赠与”珀尔,让后来移居欧洲并嫁给贵族的白兰和珀尔过上了幸福的生活。
如此一波三折的“诡异”故事,即便是从女方与“私生女”皆大欢喜的结局来看,是不是显得有点力挺“婚外情”呢?你认为这不是“通奸”而是对“爱”的坚定追求吗? (持续了七年。)
尤其是故事的结局以及涉及这起“婚外情”的三方的“处理”。坚持“爱”的白兰终于过上了幸福的生活,而懦弱、逃避责任和爱情的亚瑟却在自己和“敌人”之间挣扎。他死于肉体和精神的折磨。看似最无辜的“受害者”宁波市私家侦探,他的原配丈夫齐灵渥斯,被解读为“恶魔”复仇者的化身,并因此抑郁而死。
正当“真相”最终揭晓时,白兰七年的“对爱情的执着”不仅改变了她胸前佩戴的红色“A”的含义。
从最初的“通奸”(即Adultery),到后来的“能干”(即Able),再引申为“令人钦佩”(即Admirable),再到或许对他们的爱(即Amorous),甚至演变成在白兰帮助过的人眼中,天使的意义。
最后,对白兰的手艺赞叹不已。就像作者霍桑从一开始就被精美的“红色A”所吸引而写下了这个故事,所以“A”的含义也成为了艺术(即艺术)的象征,当然从故事的走向来看到了“胜利在最后”,似乎有了一种进步感(即Advance)。当然,考虑到《红字》170年来经久不衰的受欢迎程度,或许它也能代表美国(即美国)。
这些看似零散、含义完全不同的“解释”,或许正是霍桑在美国文学史上首创的“象征主义小说”《红字》的魅力所在。
是的,每个读者都能在其中读到自己想要的“味道”。
在接受“通奸”惩罚的同时,坚持用“婚外情”包裹着“爱情”,对“清教”教义和人性的思考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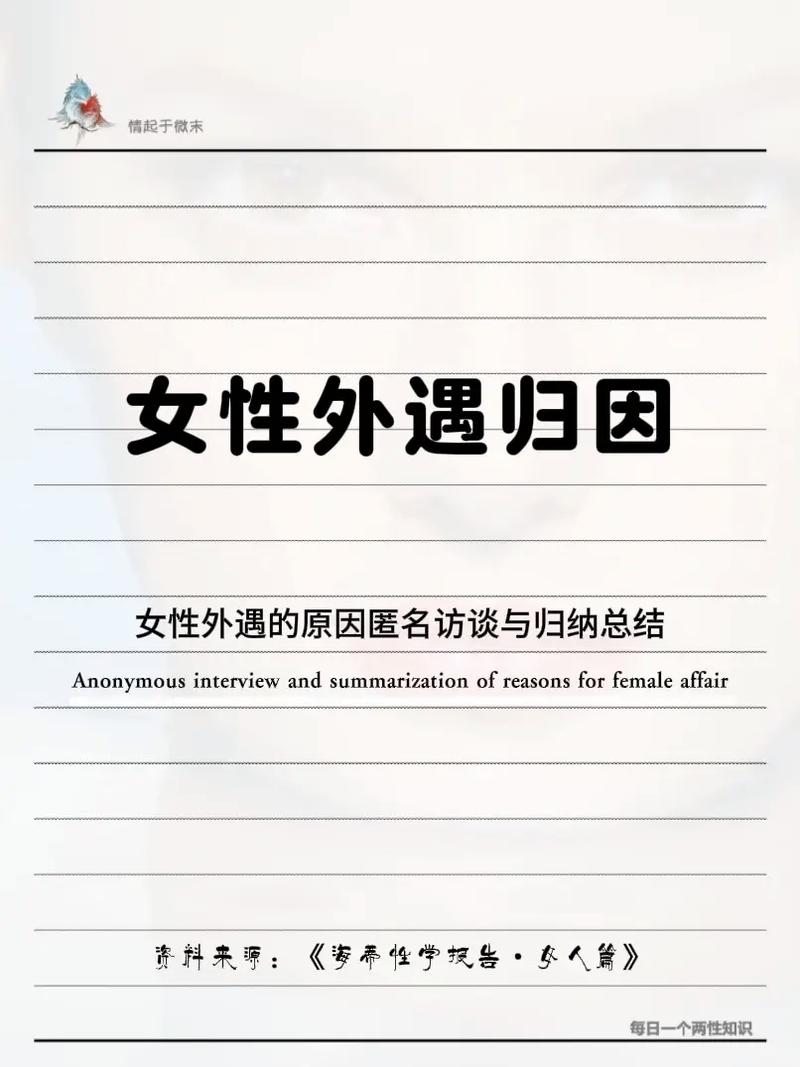
《红字》出版170年来,在读者和评论家的笔下始终被众多学派的猜测所包围。尤其是在保守“自由主义”、“现实主义”思潮盛行的时代,甚至被贴上“异端”的非议,也正是因为上述对这起看似“婚外情”的“偏见”结局的处理。
换个角度,从“罪与罚”、“救赎与被救赎”的宗教角度来看,似乎有着完全“不同”的解释。
例如,《红字》的译者胡允衡先生在序言中认为,白兰是有形的红字,亚瑟是无形的红字,齐灵渥斯是红字的制造者,珀尔是红字的制造者。活生生的红字。